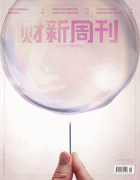中国的整体债务比GDP已经高达225%,在世界上高居榜首。其实已经落入过度借贷的陷阱。有人说中国负债过度的是企业,政府的债务并不高。
正常情况下也许如此,但前英国金融服务局负责人特纳勋爵最近指出,债务不会消失,只会转移。如果发生危机,企业债务很容易就会转化为政府债务。当然会绕弯子,比如先转化为债权银行的持股,等到银行业资不抵债了,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,到那时才最终完成由企业债务到政府债务的转换过程。所以说,眼下面临的问题,不是如何避免落入债务陷阱,而是如何走出过度借贷的陷阱。
最近连续曝出企业债券到期不能兑付的消息,已经引起了债券市场的恐慌,不但新债券发行大面积取消,偿债危机还有传导到银行的危险。现在很难说,到期债券不能兑付,到底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契机,还是扣响了系统性债务危机的扳机?
要想化解债务危机,走出过度借贷的陷阱,首先需要了解当初是如何落入陷阱的。否则即使躲过了一劫,还会重蹈覆辙。
中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生态简直就是过度借贷的沃土。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软预算约束和刚性兑付的痼疾,是过度借贷的根本原因。在这个环境下,企业举债无度,因为不必担心到期无法兑付而破产清盘,它们知道政府不会见死不救;金融机构为了扩张,对债务人的风险熟视无睹,竞相放贷,也不必担心钱放出去了收不回来;监管当局把监管对象的扩张当作自己的业绩,任凭野蛮增长,无序扩张;各级政府都有“金融支持实体经济”的诉求,甚至诉诸威胁利诱,鼓励金融机构在自己的辖区内放贷。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政银协议、政保协议等。总之,在这样的氛围里,不落入过度借贷的陷阱,是不可能的。
现在流行的说法是,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中国历来的古训是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然而,由于政府的职能错位,导致中国信用文化扭曲,信贷纪律涣散,债务人举债时无所顾忌,拖欠时也不必为后果负责,企业债务最终转化成公共债务。
由此可见,在中国重塑健康的信用文化,让债务人为拖欠债务承担损失的责任,是迟早要交的作业。中国落入债务陷阱的根本原因,除了政府的职能错位,还有迟迟不到位的预算体制改革,包括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和相应的预算制度安排。于是,各种准财政功能,就落到了金融系统的头上。
对到期不能兑付的债务重组,是千金难买的机会,不能轻易浪费了。重组债务的同时,要追查陷入债务困境的原因,追本溯源地探究体制和制度的弊端,追查内部控制的漏洞,要让所有的利害相关方重新审视其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,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做出整改;要让拖欠的企业切实感到痛苦,让管理者付出代价;也要让投资者学到教训,而不是让银行在理财资金池子里把拖欠的本金和利息消化于无形。
如果未来要防止借贷过度,还要借助金融基础设施的帮助。中央银行的企业债务登记查询系统,应该能够反映企业和行业的信贷集中程度,避免银行扎堆儿为单一企业兜售贷款。
在所有的金融基础设施里,信用评级是防止过度借贷的利器。可惜,信用评级被中国人玩儿坏了。所有的利害相关方都有动力和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,试图影响信用评级的结果。有人甚至把信用评级当作可以操纵的工具,跃跃欲试地要么想创办自己能主导的信用评级公司,要么想象着对信用评级行业施加监管。这些都为信用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投下了阴影。
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,背后都有个资金池子。池子无论大小,都可以藏污纳垢。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实体经济发生困难,银行靠销售理财产品吸收来的资金,已经很难指望获得太高的利息收入。但要维持理财产品资金池子的流动性,银行又不得不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率。于是,有些理财产品收益微薄甚至倒挂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再让银行的理财资金池子消化拖欠企业的债务,要不了多久,这种违背市场化原则的带有行政安排色彩的债务重组,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。
相关报道:债券违约临界点
版面编辑:王丽琨(ZN029)